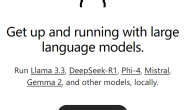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
但是,在笃信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绝对的怀疑
Descartes的哲学历程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历程。他的哲学追求的起点是对人类认知能力最根本、最彻底的怀疑。Descartes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维历程的开端:“一切迄今我以为最接近于‘真实’的东西都来自感觉和对感觉的传达。但是,我发现,这些东西常常欺骗我们。因此,唯一明智的是:再也不完全信赖那些哪怕仅仅欺骗过我们一次的东西。”外部世界对我们的认知的帮助是这样的不可信赖,那么,我们的主动感知活动(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叫做“实践”)和思维是怎样的呢?这些活动也常常出现在梦境之中,使得我们无法确切地区分“梦”与“醒”。因此,我不得不怀疑,整个的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梦幻(我们记得庄子与蝴蝶的故事)。
从这些简单、初步的“疑点”出发,Descartes把他的怀疑推到极致:“我愿意假定,一切真理的源泉不是仁慈的上帝,而是一个同样狡猾、同样有法力的恶魔,施尽全身的解数,要将我引上歧途。我愿假定,天空、空气、土地、形状、色彩、声音和一切外在事物都不过是那欺人的梦境的呈现,而那个恶魔就是要利用这些来换取我的轻信。我要这样来观察自己:好像我既没有双手,也没有双眼,也没有肉体,也没有血液,也没有一切的器官,而仅仅是糊涂地相信这些的存在。”(《Discours de la Methode》)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Descartes的怀疑不是对某些具体事物、具体原理的怀疑,而是对人类、对世界、对上帝的绝对的怀疑。从这个绝对的怀疑,Descartes要引导出不容置疑的哲学的原则。
由“思”而知“在”
Descartes接着说:“正当我企图相信这一起都是虚假的同时,我发现:有些东西(对于我的怀疑)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那个正在思维的我’!由于‘我思,故我在’这个事实超越了一切怀疑论者的怀疑,我将把它作为我所追求的哲学第一条原理。” 《Discours de la Methode》
通过Descartes对自己哲学历程的细腻描述,我们可以明白地知道,这句名言的含义不是:由于我思考,所以我存在。而是:通过思考而意识到了(我的)存在,由“思”而知“在”。
“我思,故我在”的中文的表述是很含糊、不确切的,我们的同胞的对哲学大师Descartes的误解基本上是这个中文表述所导致的。不过,在这件事上,我们中国人并不是哲学世界中唯一的迷途羔羊,几百年来,欧洲哲学界也是这样看待他的。造成这个误解的根源是Descartes的法文名著《Discours de la Methode》的拉丁文翻译。在这本书的拉丁译文中赫然可见: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假如在翻译这句话时去掉表示“我”的ergo,而直接译成cogitans sum大概比较合乎原意)。由于当时的哲学著作绝大部分使用拉丁文,而法文只是一种地方语言,从此,这句拉丁文不胫而走,成了Descartes哲学的代名词,而那法文的原文je pense, donc je suis反而淹没不张了。Descartes的初衷是建立一个不容置疑的学术方法体系,而他哲学原则的出发点首先就遭到了广泛的误解,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公平。
从翻译的困难看中国人学习欧洲哲学的可能性
从这个历史的误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训:翻译乃是很不可靠的!原文越是准确、越是有光彩,其译文与原文的差距就越大,文学作品如此,思想、哲学作品尤其如此。
翻译有两个不能逾越的障碍:第一是语言的障碍,第二是文化的障碍。二十世纪以来,语言的障碍常常被中国的学者忽略。他们以为,任何外文著作,特别是非文学著作都是可以翻译的。他们把语言看作是一个传达逻辑信息的工具系统,以为世界上一切语言都不过是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掌握了这些词汇和语法,就掌握了这个语言。这种对语言的科学的和机械的认识很具有我们时代精神的特色,也被贯穿在外语教学中。
与文化的障碍相比较起来,语言的障碍的实在仅仅是“小菜一碟”。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引征的经典,联系到的日常生活,乃至于风俗习惯,特别是千百年来沉积下来的思维模式,都具有着高度的“个性”,使得把一个作品完整地平移到另一语言和文化环境的工程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业。
任何的一个翻译传达的首先不是作者的思想,而是译者的理解、译者的能力。假如这位译者是个脚踩两条船,优游于几个文化之间的仙人(这样的人或者没有,或者凤毛麟角),他的翻译就比较有机会接近原著,前提当然是他能够按奈住自己的虚荣心,全心全意地忠实原著,而不是象严复一流恶人,有意要引读者上歧途。对于读者来说,读译著永远是间接的、片面的、不可靠的!一切严肃认真的学者都要努力去读原著!
因此,我从根本上怀疑中国人接受欧洲思想,甚至把它们作为自己未来文化的主导的可能性。
中学西用的可能性
几十年来,我们通过日语从欧洲语言借来了一大批哲学词汇,学来了一套“哲学方法”。这些词汇和方法从此成了我们研究、讨论一切有关思想的题目的基本工具,离开了他们,我们既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头脑空空,哑口无言。“西学中用”变成了拿中国的文化片断去印证西学的理论。西学在于我们早已经不仅是“用”,而变成了我们的“主心骨儿”了。这其实并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必然性,更没有思想、文化上的必然性。
通过对Descartes的哲学原理的思考,我体会到道,中国汉学的好传统:从原文入手,从文字入手,以考据为主,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传注,以求从中获得真谛,也同样适用于对欧洲古典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同时,汉学的很多方法与研究成果,比如对上古与近代语音的变迁的揭示,对西方学界也可以很有帮助。“中学西用”完全不是偶然得来的匪夷之思。但是,学界的交流与“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民族主义毫无相关,我们要坚决避免一夜之间从洋奴变成沙文主义者!
PS: 这篇小文的主要内容来自我当年的哲学读书随笔《Momente des Lebens(生命的瞬间)》,原系德文。时间历久,对引文的记忆有误差的地方恳请大家原谅。